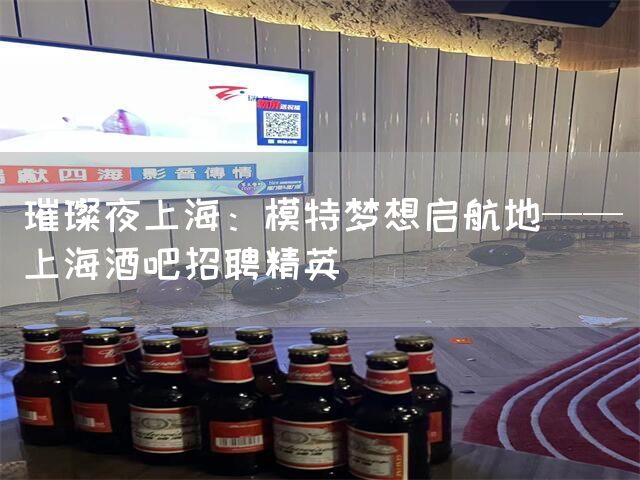国际标准书号:
我们从小就听过无数别人讲的故事,我们自己也给别人讲过我们听过的故事或者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读小说、听广播、看电视节目、看电影,我们都在获取故事。 。 可以说,故事几乎无处不在。 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故事引入了叙事的概念。 故事与叙事不同(尽管经常混为一谈),后者“指的是一种交流关系,是实现象征性表征的一种特定方式”。
保罗·科布利的《叙事》一书致力于将叙事置于表征的一般过程中,并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讨论叙事作为一种表征模式。 建构主义认为意义既不受表征形式的发出者的控制,也不受事物表征的控制,而是强调意义建构的彻底社会性,并认为推动意义的实际上是表征系统而不是使用者和客体。 本书分为九章。
第一章首先区分“故事”、“情节”、“叙事”等容易混淆的概念,然后讨论叙事与事件顺序、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简单地说,故事包含了要描述的事件,情节是决定这些事件如何相互联系的因果链,因此是根据这些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来描述的。 叙述是对这些事件的展示或讲述,以及展示或讲述所采用的方式。 叙事,简单地说,就是从起点A到终点B的运动,是一个涉及叙事空间和时间的序列。 时间的问题。 叙事必须走向结局,但这个过程不能简单地是一次性的顺利到达,而是“通过模糊、设置陷阱或给出错误的回答来减慢叙事进程”。 在这个拖延的过程中,仿佛叙事占据了一个空间。 叙事中的时间并不遵循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相信的简单的线性顺序。 叙述的终点非常重要。 它不仅创造了一种束缚力,使叙事在走向终点时出现迂回和阻塞,而且决定了叙事中的连续行为,使得叙事不仅关注时间线上的个别问题,更重要的是期待和记忆。
第二章回顾了早期的叙事,重点关注荷马和圣经,以及处理和探索这些叙事时遇到的问题。 叙事分析本身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叙事不仅用于记录虚构事件,还用于记录非虚构事件。 现在看来,虚构与非虚构很容易区分,但当叙事所记录的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时,这就给叙事分析带来了一些困难。 我们必须清楚,叙事不同于小说:首先,历史话语是关于真实发生的事情,但历史学家在解释真实事件的过程及其因果规律的实践中灌输叙事。 其次,需要考虑早期文化实现叙事形式的可能目的。 对于早期文化,即那些没有文字但想要保存其历史、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来说,叙事被认为是记忆的辅助手段,非常有价值。 荷马早期的主要叙述与《圣经》之间的区别在于,《圣经》留下了大量的细节没有解释。 这是一种“解释性”叙事,邀请读者解释直接陈述的内容,而荷马叙事则提供了大量细节。 信息,从而阻碍读者或听众的解释。 同时,《圣经》中的人物是“多维的”,但这种多维性在荷马的叙述中并没有呈现,荷马的叙述更注重事件。
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介绍了小说的典型叙事。 第三章一开始首先讨论了柏拉图的模仿理论。 对于柏拉图来说,模仿不仅仅包括艺术或诗歌中的模仿模式,而是指一种非常普遍的描述行为,即世界的“永恒模式”。 戏仿通常被认为是对事件和人物的戏剧性模仿,只是向读者或观众展示叙述中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报告事件和人物,讲述叙述中发生的事情并与诗人的声音相关。 荷马的史诗被认为将模仿模式与诗人的声音相结合,构成了表现世界的有力方式。 这种混合模式也在后来的小说中得到发展。 随着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和识字率的提高,小说的叙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9世纪,现实主义和小说发展成为主要的叙事形式。 现实主义小说十分关注社会背景,探讨可识别的社会结构中个体之间的关系。 探索这些关系的工具仍然是模仿和叙述者的声音之间。 相互作用。 现实主义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问题在于,现实主义的“现实”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并不像他们想要准确描述的那样“真实”。 作者反复强调,叙事是一种再现,而这种再现过程必然涉及到一些事物被选择性地再现,而另一些则没有。 在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中,叙述者操纵和构建他或她自己的现实版本。 例如,在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文本《米德尔马契》中,就有强烈的叙事声音。 “所有角色的言语都由叙述者的声音控制和操纵,叙述者占据了语音层次的最高级别。” ”。 然而,根据巴赫金的说法,小说是复调的,由多种不同的声音组成,其中一些声音有时会相互竞争,而它们之间潜在的竞争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叠。 因此,在巴赫金看来,叙述者的声音主导和控制小说并不是必然的。 当叙述者的权威声音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声音重叠时,他的权威就会受到质疑,读者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控制小说。 寻求权威并无视叙述者命令的地方。 因此,对话性是人们之间传播的符号的决定性特征,构成叙事的符号不断地展开为其他符号,没有任何一个权威可以拥有和控制它们。
第五章涉及跨文化传播技术与现代主义,主要分析康拉德的《黑暗之心》。 作者承认它延续了西方叙事传统的核心:关于人物、身份和自我之旅的故事。 同时,作者在叙述中更多地考虑了帝国主义与压迫之间的关系。 帝国主义在主张文明的趋势下,充满了欲望。 文明、公平是前台,但抑制不住的是帝国主义冲动。 同时,作者还指出,《黑暗之心》的叙事戏剧性地戏剧化了20世纪初期关于人类身份的不统一和连贯性的日益增长的思想。
第六章讨论电影与另一种叙事形式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第七章重点讨论后现代主义和叙事。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密切相关,“在(后)现代性中存在着一套新的物质条件,源于大规模生产的衰落,有利于弹性专业化。信息和服务业的主权,超越传统制造业产品,强调消费”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瓦解为以“身份”为中心的政治,而通讯技术的发展帮助缩短了世界各地人们之间的距离,也让代表变得更容易接近。 在后现代主义叙事中,叙事过程中叙事者的在场构成了叙事的“断裂”效应。
第八章主要关注叙事符号的未来。 作者介绍了皮尔士的符号系统。 皮尔斯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在于它是三元的。 这些包括“符号”或“代表”、“对象”和“解释”。 “代表”可以与现实世界中的物体相关联,也可以代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而“解释者”则充当中介者,将“代表”与“物体”之间的关系解释为符号。 可能的。 皮尔士的符号学有两个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叙事。 首先,它体现了一个符号必须是某个人的符号。 符号是对话性的,它们必须始终是开放的,并且为了存在,总是受到“他者”的影响,叙事中的符号以多种方式展开,允许读者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们。 第二个解释者将“代表”与“对象”联系起来,“解释者”也可以成为“代表”,然后与“对象”联系起来,等等。 叙事因此能够超越自身。
最后一章讨论了20世纪头十年叙事和叙事分析的各种发展方向。 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环境领域。 环境领域理论认为,所有物种都生活在一个由它们自己的符号组成的世界中,后者是它们自己创造和接收符号的能力的结果。 人类环境领域呈现出三种造型: 一阶造型,源于先天分化能力的世界。 二次成型,构建一个无需语言表达的世界。 第三次造型产生于复杂文化形式的世界,以初级和二次造型为基础。 有学者指出,语言交际(二级塑造)是人类语言能力所固有的、具有敏锐辨别能力的先天(一级)塑造方法的功能变异。 叙事也是构成人类环境领域的非言语和言语符号活动的相同或相关特征的功能变异,而不是“适应”“模块”或独立的相似生物实体。 作者还指出,叙事植根于节奏、质量、非语言象征活动和一阶塑造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作者从一开始就从事件序列、时间和空间的表征来讨论网络问题,并将表征过程区分为情节、故事和叙事。 对叙事的分析被反复讨论,试图说明叙事如何以特定方式接近或规避世界。 叙事用于存储有关身份的信息,也构成文化的基础,但叙事是有选择性的,选择说一些事情而排除另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模仿模式与诗人的声音或叙述者的声音的混合构成了叙事的说教性质。 在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中,建立了一种等级制度,其中叙述者的声音淹没或削弱了人物的声音。 同时我们看到,叙述者声音的主导地位并非必然,因为叙述符号的会话性导致了开放性,说教的作者和介入的叙述者都无法限制人们接近现实的方式。 解释符号的过程。
参考:
保罗·科布利的《叙事》,方晓莉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过去的选择:
(本文发表于符号学论坛)
(图片均来自网络)